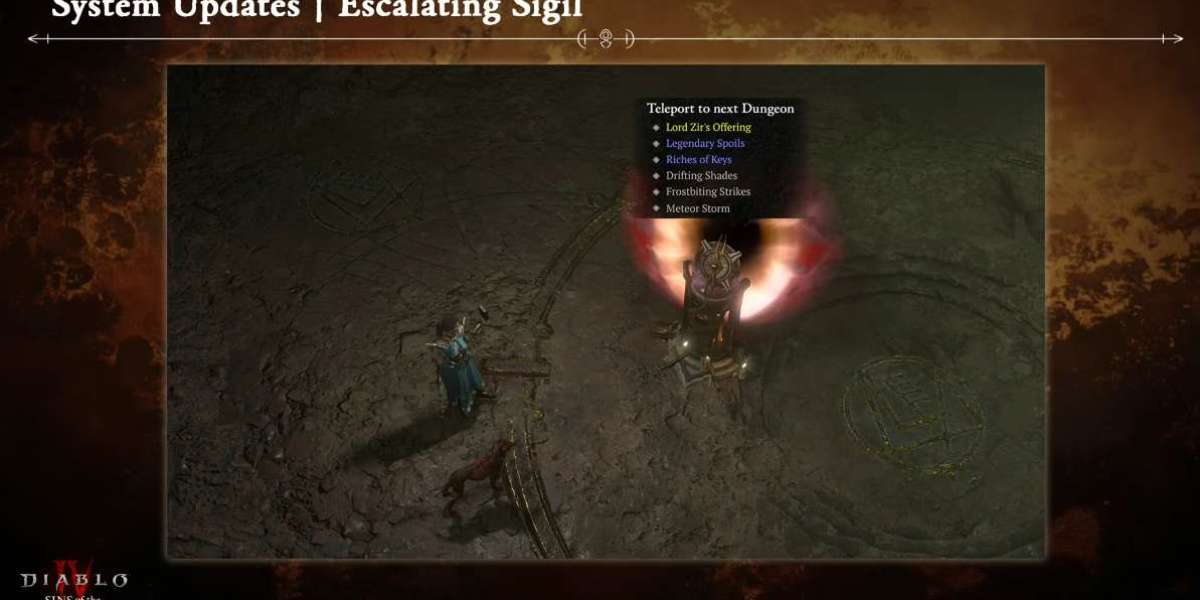| 温馨提示 |
|---|
| 这篇文章聊的话题可能有点“重”,但请相信我,读完它,你可能会像我一样,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照亮了。它无关迷信,只关乎生命、爱与告别。准备好了吗?那我们开始吧。 |
在加拿大研究死亡,是种什么体验?
还记得那是来加拿大的第二年,一个普通的周二早上。多伦多的天还没全亮,我缩在被窝里刷着手机,突然看到我妈凌晨四点(也就是我这边下午四点)发来的一条微信:“你外婆走了。”
就这么短短五个字,没有表情,没有语音。我瞬间就懵了,大脑一片空白。我外婆,那个总是在视频里笑着问我“钱够不够花”“有没有好好吃饭”的老人,就这么消失了?我甚至没来得及跟她说上一句正式的再见。
接下来的几天,我像个行尸走肉。看着朋友圈里家人发的葬礼照片,听着电话那头压抑的哭声,我却隔着一万公里的距离,什么也做不了。那种无力感和疏离感,几乎要把我吞噬。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,作为一个留学生,我们不仅错过了家人的生日和婚礼,还可能错过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告别。
也正是从那一刻起,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扎了根:我需要学习如何面对死亡,如何处理悲伤。于是,在选修课列表里看到“Thanatology: An Introduction to Death and Dying”(死亡学导论)时,我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了它。我身边的朋友都惊呆了,一个学会计的跑去研究死亡,是不是疯了?他们劝我,这玩意儿又“不吉利”又找不到工作,还不如多刷几道题。但我知道,这门课是我当时最需要的。
后来我才发现,这个决定,可能是我整个留学生活里,做过的最酷、最正确的一件事。
死亡不是禁忌,是一门正经的“生命科学”
在国内,我们从小被教育要“避讳”死亡。长辈生病了,我们说“会好起来的”;清明节扫墓,气氛总是肃穆而沉重。我们似乎默认,只要不谈论它,死亡就不会来敲门。
但在加拿大的这门课上,死亡被摊开在桌面上,成了一门可以被理性、温和地探讨的学科——Thanatology。这个词源于希腊神话里的死神塔纳托斯(Thanatos),听起来有点唬人,但它研究的范围其实特别广,涵盖了临终关怀、悲伤辅导、死亡的社会文化意义、殡葬伦理等等。它不是让你变得神神叨叨,而是教你用一个更广阔、更人文的视角去看待生命的终点。
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,尤其是在西安大略大学附属的国王大学学院(King's University College at Western University),它的死亡学研究在整个北美都赫赫有名。教授上第一节课就说:“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你们不害怕死亡,而是让你们理解它,从而更勇敢、更清醒地活着。”
课堂上没有阴森恐怖的氛围,反而充满了故事和温度。我们讨论过不同文化里千奇百怪的葬礼仪式,比如墨西哥人会开派对庆祝的“亡灵节”;我们分析过电影《入殓师》里,如何通过仪式给予逝者最后的尊严;我们甚至还小组辩论过“安乐死”在加拿大的合法化进程。根据加拿大卫生部2022年的数据,自从医疗援助死亡(MAiD)合法化以来,已有超过三万名加拿大人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难以忍受的痛苦。课堂上的讨论,让我第一次意识到,原来“如何死”和“如何活”一样,是一个值得被尊重和讨论的个人选择。
走进安宁病房,我看到了生命最后的温柔
这门课最震撼我的部分,不是理论知识,而是田野调查(Field Study)——去本地的安宁疗护中心(Hospice)做志愿者。
去之前,我把Hospice想象成一个充满消毒水味、气氛压抑的“等死”的地方。可当我推开那扇门时,迎接我的是暖黄色的灯光、空气中飘着的咖啡香,还有志愿者在客厅弹着吉他。这里不像医院,更像一个温暖的家。住在这里的,都是生命只剩下不到六个月的病人。
我的任务很简单,就是陪伴。陪他们聊聊天,读读报纸,或者只是安静地坐着。我遇到的第一个“伙伴”是87岁的艾伦爷爷,一个退役的空军工程师,因为癌症晚期住在这里。他很瘦,说话很慢,但眼睛里总是闪着光。
他会给我讲他年轻时开战斗机的故事,讲他和他去世五十年的妻子是如何一见钟情的。他从不抱怨病痛,反而对我说:“我这一生,去过很多地方,爱过一个人,有一个爱我的女儿,够了。现在我只是有点累,想休息了。”
有一次,我问他,在这里会不会感到害怕。他指了指窗外,一只知更鸟正落在喂鸟器上。“你看,”他说,“每天早上,它都会来。太阳也会升起来。我走了,它们也还会在。世界不会因为我而停止,这挺好的,不是吗?说明我来过,并且参与过一个很棒的系统。”
那一刻,我鼻子一酸。艾伦爷爷让我明白,临终关怀(Palliative Care)的核心,不是治愈疾病,而是减轻痛苦,维护尊严,让生命在最后的旅程里,依然能感受到平静和美好。然而,现实是残酷的。根据加拿大临终关怀协会(CHPCA)的数据,尽管加拿大超过85%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,但只有不到30%的加拿大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临终关怀服务。尤其是在一些偏远社区和原住民社区,资源更是稀缺。这意味着,还有太多像艾伦爷爷一样的人,在生命的最后阶段,无法得到应有的支持。
在Hospice的三个月,我见证了生命的脆弱,但更多的是坚韧和爱。我看到家人们围坐在一起,为病人唱他最喜欢的歌;我看到护士温柔地为病人擦拭身体,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;我看到一个5岁的小女孩,在画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太阳,贴在她奶奶的床头。
死亡在这里不是一个冰冷的结果,而是一个被温柔和爱包围的过程。它教会我,告别不一定都要撕心裂肺,也可以是平静地、充满感激地,说一声“谢谢你,再见”。
学习悲伤,是每个留学生的必修课
你有没有觉得,留学生活就像一场漫长的“告别”练习?告别父母,告别朋友,告别熟悉的环境,甚至告别过去的自己。我们每个人心里,都或多或少积压着一些没有被好好处理的“悲伤”。
这门课有一个重要的单元,叫“Grief and Bereavement”(悲伤与丧亲)。教授告诉我们,悲伤不是一种需要被“克服”的疾病,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。它没有标准流程,也没有时间限制。你可能会愤怒,可能会麻木,可能会突然在某个深夜崩溃大哭,这都OK。
我们学习了各种悲伤辅导的理论,但最有用的一个理念,叫做“陪伴者模式”(Companioning Model)。这个理论认为,悲伤辅导员的角色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“专家”,去“修复”别人的悲伤,而是一个“同路人”,安静地陪着对方走过这段幽暗的隧道。你不需要给出建议,不需要说“别难过了”,你只需要倾听,并让他们知道“你不是一个人”。
这个理念简直是为我们这群留学生量身定做的。根据加拿大国际教育局(CBIE)的一项调查,超过40%的国际学生在加拿大感到孤独和孤立。当我们遇到困难,无论是学业压力、感情问题,还是像我一样经历亲人离世,我们常常选择自己硬扛,因为不想让远方的父母担心。
学了这门课后,我和朋友们的相处模式都变了。当朋友失恋了找我哭诉,我不再笨拙地劝她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,而是给她一个拥抱,说:“我知道这很难受,想哭就哭吧,我陪着你。”当我自己因为想家而情绪低落时,我也会勇敢地告诉朋友:“我今天心情不太好,能跟你聊聊吗?”
我们开始学习如何成为彼此的“陪伴者”。这种守望相助,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。原来,真正治愈悲伤的,不是时间,而是爱与连接。
当东方“孝道”遇见西方“自主”
作为一个中国学生,在这门课上,我经常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。尤其是在讨论“生命末期决策”(End-of-life Decision Making)时。
在加拿大,个人自主权被看得非常重。成年人有权提前签署预立医疗指示(Advance Care Directive),明确说明在自己无法表达意愿时,希望或不希望接受哪些医疗救治,比如是否使用呼吸机、是否进行心肺复苏等。这被认为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表现。
但在我们的文化里,这事儿就复杂多了。“孝”文化根深蒂固,我们觉得,只要父母还有一口气,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,否则就是“不孝”。让父母提前决定“放弃治疗”,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,甚至是大逆不道的。
课堂上,我和一个本地同学有过一次激烈的讨论。他认为,延长没有质量的生命是对病人的一种折磨。我则反驳,对家人来说,哪怕父母只是躺在病床上,只要他们还在,家就在。我们争得面红耳赤,最后谁也没说服谁。
下课后,教授把我叫到一边,她对我说:“你的观点没有错,他的也没有。这背后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,一个是集体主义,一个是个人主义。没有谁比谁更高级。重要的是,我们能否理解并尊重彼此的选择。”
她的话让我茅塞顿开。我开始反思,我们所谓的“孝顺”,有多少是真正出于对父母意愿的尊重,又有多少是源于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社会的压力?如果我爱我的父母,我是否应该在他们还健康、清醒的时候,就和他们聊一聊这个话题?问问他们,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?
这门课没有给我一个标准答案,但它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,让我学会跳出自己固有的文化框架去思考问题。它让我明白,真正的爱,不是替他们做决定,而是支持他们做出自己的决定。
留学,不只是为了卷一个未来
我知道,看到这里,你可能会问:学这个专业,到底能干嘛?能进大厂吗?能移民吗?
坦白说,它确实不是一个热门的“高薪”专业。毕业生的去向大多是医院的社工、临终关怀中心的协调员、悲伤辅导顾问、殡葬行业的从业者,或者是进入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,从事相关的政策研究。比如,在加拿大,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(预计到2030年,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3%),对临终关怀和老年服务的需求正在爆炸式增长,这其实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。
但对我来说,这门课最大的价值,不在于它给了我一张通往某个职业的门票,而在于它彻底改变了我看世界的方式。
它就像给我戴上了一副新的眼镜。当我走在街上,看到步履蹒跚的老人,我不再只看到衰老,而是会想象他们背后那漫长而丰富的人生故事。当我看到新闻里天灾人祸的报道,我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,而是能更深地共情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所经历的痛苦。当我再面对自己的生活,我开始认真思考: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一年,我会做什么?
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给家人打电话,不再是敷衍的几句问候,而是认真地听他们分享生活的琐碎。我开始学着记录下生活中的小确幸,哪怕只是一顿美味的晚餐,或是一次和朋友的开怀大笑。我不再为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焦虑,而是把精力聚焦于当下我能做的事。
“Memento mori”——这是一个古老的拉丁语谚语,意思是“记住你终将死去”。听起来有点丧,但它其实是最强大的生命激励。正是因为生命有限,我们才要更热烈、更真诚、更勇敢地去爱,去体验,去创造。
如果你也厌倦了在CS和商科的内卷中迷失自己,如果你也想在留学生活中,寻找一些更触及灵魂的东西,那不妨去你们学校的选课系统里搜一搜,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课程。可能只是一个学分的选修课,但它带给你的震撼和成长,可能会让你受益终生。
毕竟,留学一场,我们不只是为了拿一个学位,更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完整、更懂得如何去爱的人,不是吗?